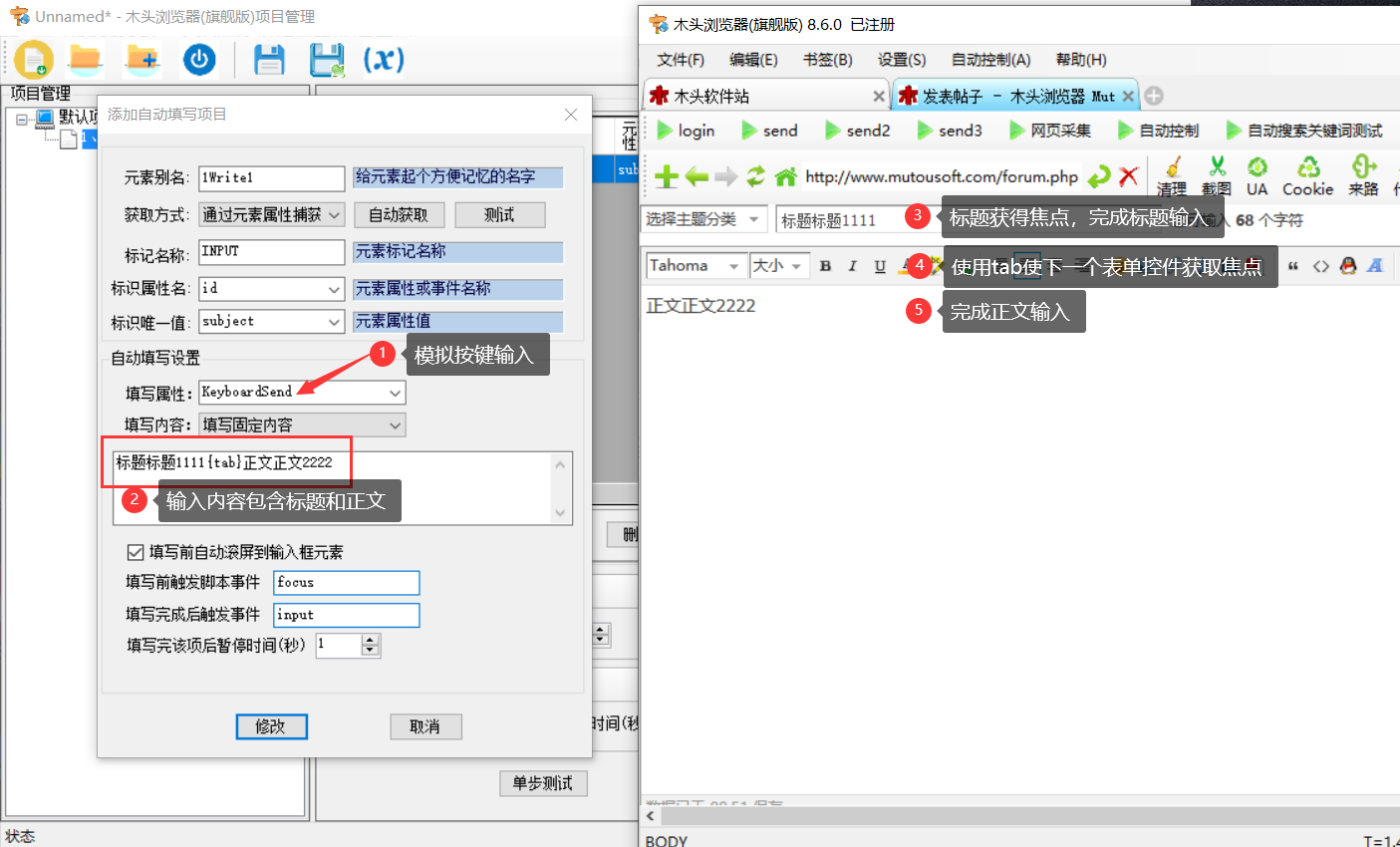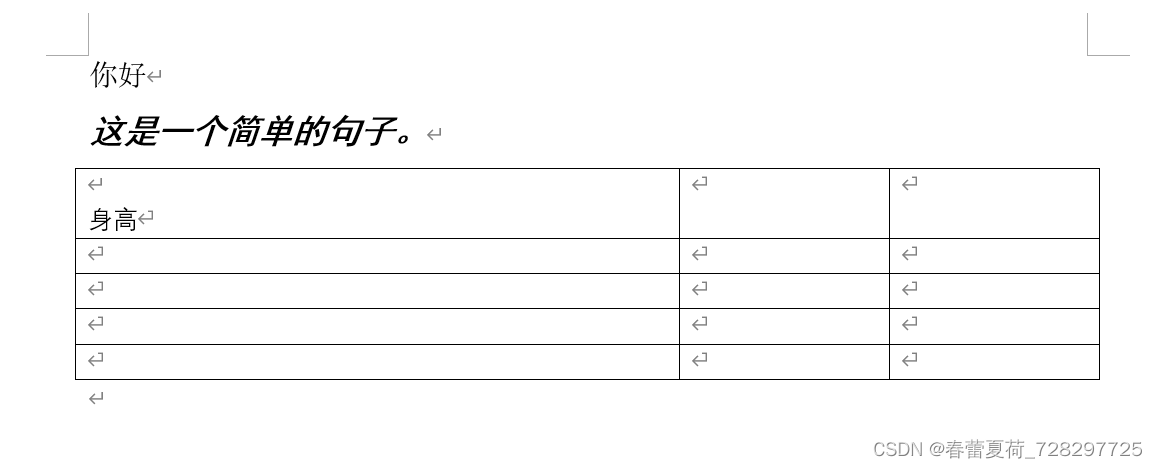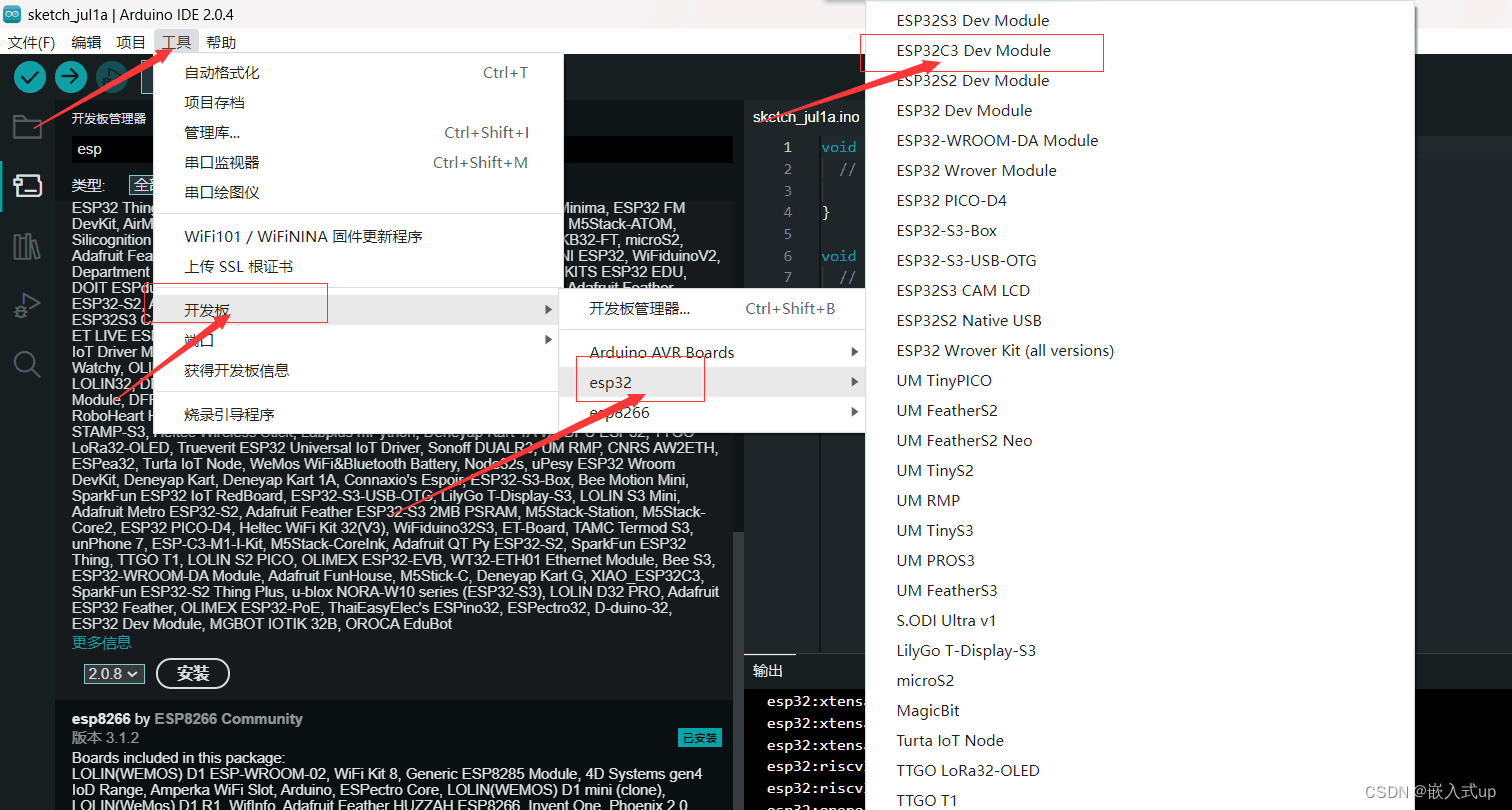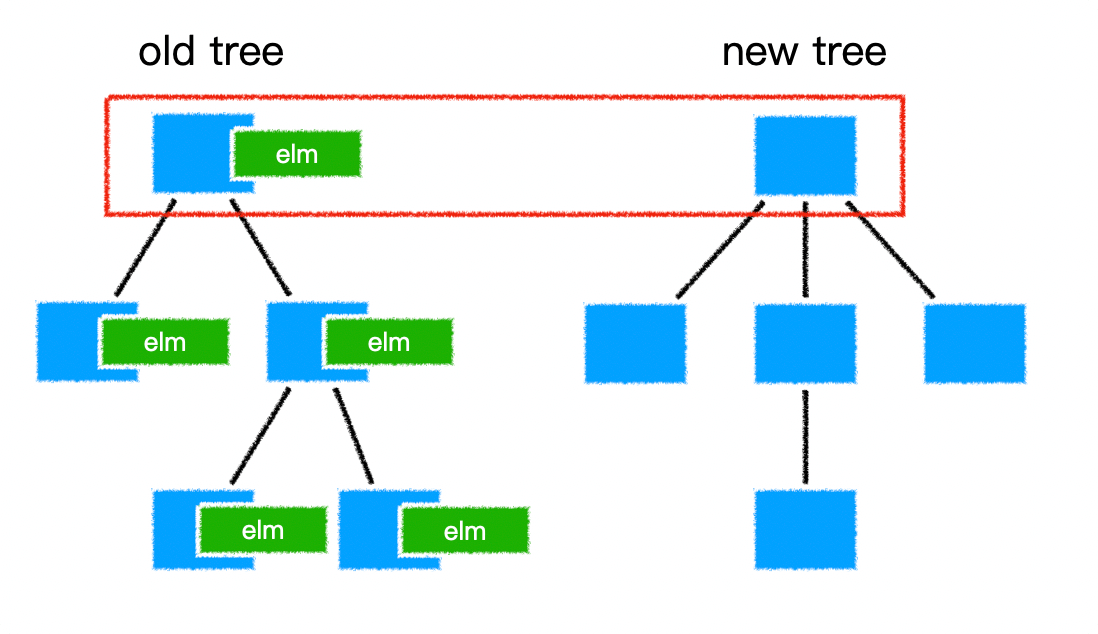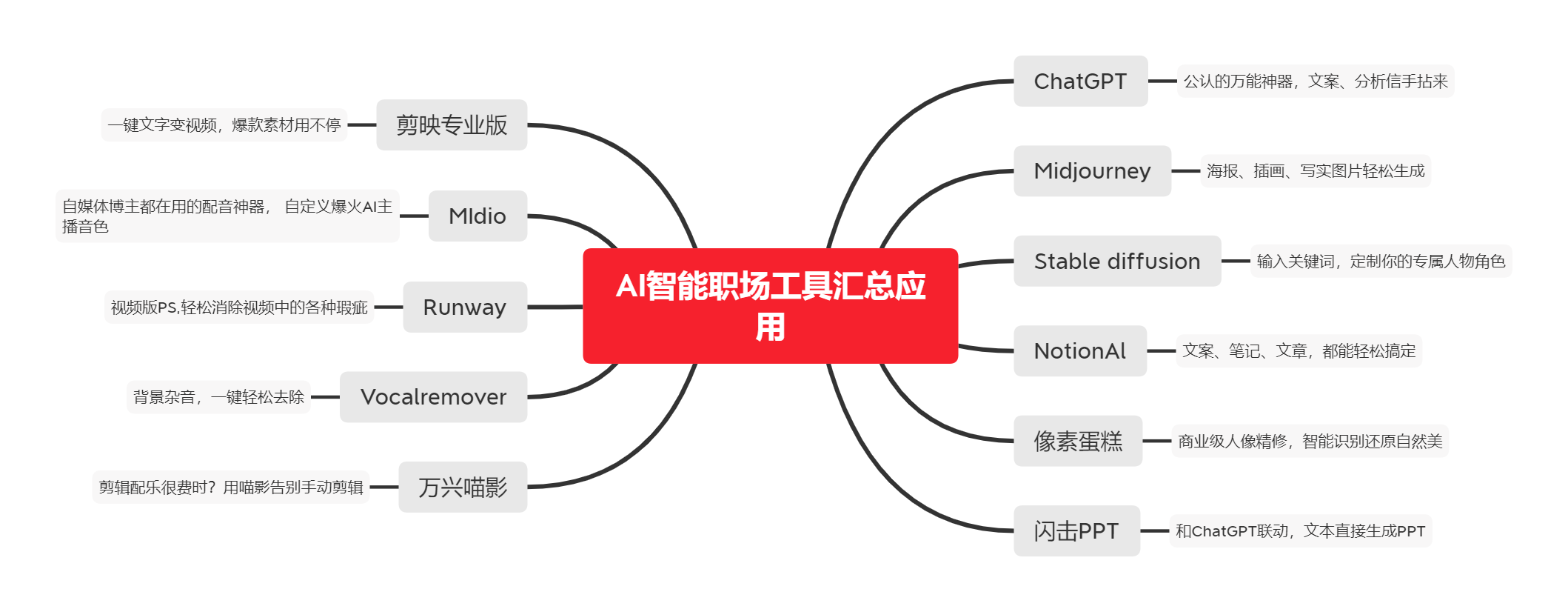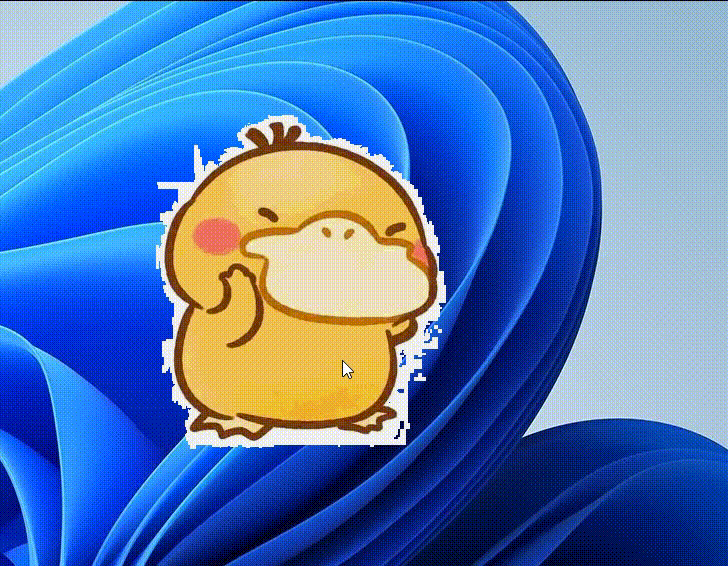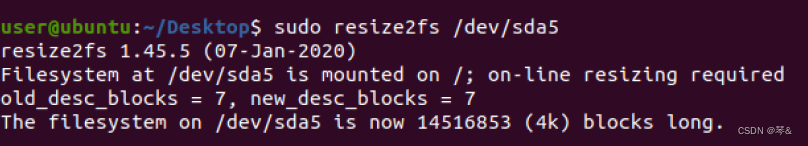少年时代的记忆是最模糊的,却也是最深刻的。一些瞬间在大脑里几十年,那一定是你曾经心动和在乎过的感受。年少求学期间,因对数学的痴迷,和数学有关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记得一个人趴在地上解题一下午的投入,记得因数学获得的一切掌声和荣耀,记得每一次数学之美浸润心脾的畅快,也记得每一个教过我的数学老师。
语文王老师在我高考前的周记作文本里曾感慨评价道:“语文即是人生!”不过还是怪自己没能开窍,只能磕磕绊绊地走在了“数学即是人生”的道路上。学数学,做数学题,讲数学题,是我年少时的半条命,还有半条,是魔术。
朱哥是我在雅礼读书时候的高中数学竞赛教练。由于他段位太高,直到初三以前,我们大多数同学也没机会上过他的课,只听说他是未来高中数学竞赛组的负责老师,大boss。自发自然地,把数学和数学竞赛深耕下去,成了我天然的动力,以后能进到朱老师组真的搞数学竞赛,也成了心中图腾。我和朱哥的故事,也就从那时说起。
知遇之恩
数学竞赛的竞争是惨烈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处在什么位置,学这个的现实ROI如何,只知那是我唯一热爱的东西。大约是小学二年级一次周末的奥数课上,那个胖胖的于老师一句“说的非常精彩”,让我尝到了甜头;上初中的陈老师的一句“你的优秀和平常人不一样”让我开启了自我强化的认证模式,但是这都是牛刀小试了。到初三评直升名额,待准备考省理班疯狂补奥数的时候,我在朱老师的奥数课上也终于并非最突出的那几个了,似乎自己也没得到他太多关注。谈不上气馁,但就一直本能地默默努力。
后来,在一次突击的奥数考试后的一个课间,班主任数学陈老师从教室外走廊的尽头开始就兴高采烈地在朝我看,飞奔过来说:“你知道吗?你这次考的非常好,被朱老师看重了,可要好好把握机会,进省理班,进数学组啊!”至今还记得旁边的钟同学那羡慕又鄙夷的眼神,至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在我印象里,那次考得很一般,但这给了我要把这个恍惚变成现实的信心。
可惜到直升后的一个暑假,没有规律的学习使得我在考高中分班考试中的状态一落千丈。好在朱老师依旧看重我在之前的数次考试中表现出来的潜力,力排众议把我仍然选进了省理班。当然这其中具体还有什么细节我无从知道,只知道一个省理班名额的竞争,可不仅仅是考试成绩那么简单的,应该是很惊险的。虽然最后的竞赛成绩并不如愿,但这份信任给我的认同和动力却是影响巨大的,后来一不小心就把数学竞赛转化成数学模型,转化成一生的梦想。
这次,应该也是我在象牙塔的封闭环境里最后一次在可见的高位运作的人生了。之后无论是运气,还是现实带来的冲击,很真实,但再也回不去那个感觉。
模拟联合国
进到数学组以后,朱哥平日高冷和不苟言笑的风格便日趋显现,因为直到此时才真的近距离听他的课,跟着他学习高中部分的竞赛知识。那时候是感到了压力的,一种要视死如归,放弃其他一切时间,爱好,拼命的感觉。当时就有一些小伙伴还不知道厉害,在试探着朱哥的边界。
刚进数学组不久,白同学就把数学竞赛当成了他广泛爱好中的一个,并雨露均沾。在每周几节集训课的情况下,依然参加了需要逃课的模拟联合国活动,并一举夺魁。
在模联讲台上多慷慨激昂,在朱哥的课堂上就有多灰头土脸。小白参加完活动回来,还沉浸在演讲完的兴奋中,只见朱老师经典地阴沉着脸说:
“你干嘛去了?”
小白本以为有人要分享他的喜悦,然后却感到一丝寒意:
“去......去......去参加模联了......”
“搞什么搞,想搞竞赛,还想搞模联,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随后丢下一个人影走了,只留下小白和我们坐在座位上发愣。
妈呀,我和菜哥赶紧收起桌子底下刚变完魔术的扑克牌,并在数学组的教室里,再也没敢打开过。
回忆起来,那时我们有多瘆得慌,现在就是一个多好笑又温暖的梗。对待事关前途和荣誉的竞争,他带着我们拿出了最顶级的要求和态度,见识到了拼搏的样子并去习这珍贵的品质。也正因为此,筛选出了真的有兴趣和能力的雅礼人,一届一届地持续地让雅礼以我为荣。
dy/dx的奇闻
随着和朱哥的日渐熟悉,课堂上我们有时也敢开开玩笑和活跃活跃气氛了。但朱哥似乎不喜欢这样,不管是憋着笑还是真的笑点高,总是一副严肃并表达出我才是这里的老大,我最厉害的感觉,并鼓足劲要随时证明这一点。大概是高一时候,刚引入导数的相关知识。他讲解道:
“导数在课本里讲的是切线斜率,是割线无限接近它的情况。但那只是直观,不是真的定义。”
然后写下:
y = f'(x),并表现得不情愿地画了几条割线,逐渐趋近于切线的样子。
然后忽然顿了一下,憋住了轻微上扬的嘴角:
“其实吧,导数就是微分的商,书上那个定义不准确。”
然后煞有介事地写上y' = dy / dx
“注意啊,这不是除法,是微分的商,反正你们也不懂。”
又憋着得意了几秒钟:
“但是可以移过来,写成:”
dy = y’ dx
然后台下的同学们就全疯了。在完全还没有微积分概念的我们脑海里,就这么轻易地被朱哥又上了一课,就问你们服不服。菜哥经典评价道:
“靠,老是搞些高级概念骗我们,我们不过就是晚学几年撒!”
黄同学说:
我真的服了,写成dy / dx就算了,还硬要把dx移过去,真是的,想把我们搞晕吧!
哈哈,印象中数学老师憋不住的炫技还有一次,就是屈老师在讲x ^ 3 = 1的所有复数解的时候,直接在复平面的单位圆上点了三个点,说:
“不用算了,它们都在单位圆上,并成正三角形分布。”
画完就下课走了。
哎,数学老师们啊,一般课堂上是不炫技的,除非憋不住,嘻嘻。
毕业后唯一一次相见
大学我考得很一般,最后半欺骗式地让自己报了个工科,安慰自己说工科到处都要用数学。可这安慰没过多久就成了笑话,我低估了我对数学本身的执念,我也高估了工科对待数学的态度和地位。我没法接受数学就以这样透明的工具存在于一般的工科学科里,于是便在有限的空间内疯狂地在大学里找一切能和数学沾边的事情做,哪怕在门外能多学点也能缓解我的不安全感。
于是我尝试把数学用在计量经济学,管理科学,精密加工路径的计算中,尝试着把这些都变成数学模型,有大一统的数学结构。同时疯狂地找补大学以数学光环围绕的感觉,拿下高数竞赛,全国/北美数学建模竞赛,还有一堆因为数学所获得的成绩。
在大一假期一次回家的同学聚会中,我终于又见到了朱哥,我掏出了这一年来获得的各种数学证书,厚厚一沓,认真地和他说:
“对不起,那时候我扛不住压力选择了高考,退出了数学组,但我最爱的依旧是数学,你看!”
朱哥缓缓地翻阅着这些奖状和证书,也一字一顿,缓缓地说道:
“嗯,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也知足了,谢谢你!”
然后我还终于鼓起勇气掏出了当年没敢掏出的扑克牌,给他变了Jumping Gemini,几个double就把他吓得一愣一愣的,爽啊!
那一刻,仿佛我又回到了那个高中的孩子,又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中幸福地迷离着双眼。
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的这等体验了,因为我已经不可逆的长大,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成人的环境。在那里,数学还有用,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全方位呵护我了,我要重新向这个新的世界学习,妥协,并达成新的均衡。
还因为,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