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旭东
来 源:《民族学刊》
[摘要]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田野工作经验,将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总结为: 心存异趣、扎实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神游冥想、克己宽容以及文字天下八个方面,笔者称其为“田野八式”,也就是田野工作的八种程式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延伸出“点线结合、特征追溯、线面统一、微观聚焦”的田野工作思路。
[关键词] 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田野八式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从事实际研究的基本功,也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必备知识。借助我自己田野研究的经历以及授课经验,贡献一下从我自己的角度所理解的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做研究跟生活、工作一样,都需要工具,人类学提供的就是一种展开实地田野研究的工具。但这工具又不是简单的工具本身,实际上任何一个工具背后都是有哲学的,如果没有背后的哲学,肯定发展不出精致适用的工具,尽管这种哲学不一定都是能够明确写下来的。比如车轮为什么是圆的这样一个问题,最早的人类可能没有想到车轮可以是圆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才发现车轮做成圆的会比较好。各种工具背后所隐含的哲学思想是什么,这可能就是各大文明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样,在中国,因为有了毛笔这个工具,才培养出中国那套“士”的风范,或者至少是一个影响的要素。现在我们每天都像工人一样在敲文字,智能化的工具越来越缺少毛笔的那份儒雅的魅力,这也可能是使得日常的生活变得单调、无聊和乏味的原因之一吧。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上。在人类学研究中,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里要论述的田野研究方法,它成为了现代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显然,人类学跟别的学科不一样是因为它有“田野”,其他的学科学习这种田野工作的方法,就变成了各种人类学的不同分支,法律人类学当然也不例外。只要是在谈到这个田野工作的方法的时候,每个人类学家都可以很自豪地对别的学科的人说: “那是我的田野,我待了一年,你没有吧,那就得听我的”。
说到田野研究方法,我想,最好的方法和工具都应该是属于自己专门制造出来的。但方法上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你要在现场,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针对现代的人类学而言。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不同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要去感受,可能有时一句话都不说,但是观察到的却很多,这就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观察。参与观察中有很多的人造物,从人造物中可以发展出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我在四川大邑县老街上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一个老人在做生意,一个墙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科学取痣”四个字( 图 1) 。这时候人类学家就需要反思,这里的“科学”两个字是指的什么意思? 很多人会说,要相信科学,好像传统的那些方法就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效用,在田野中所观察到的“科学”,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不像是实验室里的实验出来的那么科学。但对普通的百姓而言,科学不科学关键问题是有没有更多的人在用这位老人的药,如果有,那就是有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生活世界中的灵验的问题,它很值得细致地研究。[1]
我曾经讲过两三个学期的“田野工作方法”这门课,为了便于知识的梳理和对田野工作的理解,我曾专门对此一方法的内涵做了一些知识上的整理,算是对这样一种方法的中国意识的总结,我把它称为“田野八式”,也就是田野工作的八种程式或方法,这分别是心存异趣、扎实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神游冥想、克己宽容以及文字天下。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这入个个方去对人类学类田野工作方法进行一种归类,便于我们的学生理解和掌握。下面我就很简略的说明一下这些我眼中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一、“心存异趣”
显然,一个人对于外部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激情,是不可能做人类学的,或者不可能会有社会科学的原创性的发现。这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你对人类学感兴趣,首先就要对一个跟你每天衣食住行不一样的世界有一种兴奋感和激动感,这是人类学家基本素质测量的一种指标。我们招学生的时候有时就会问一些这样看起来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你吃老鼠肉吗?”假人类学家气质的学生就会回答说他不吃,因为他对这个动物心生厌恶;聪明一点的学生就会回答说会吃,即使他不敢吃。不要认为这是后者在撒谎,这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态度,你不喜欢并不是直接的表露出来,而是要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礼。可能人类学最值得大家研究的内容之一就包括这撒谎了,每个人一辈子如果不撒谎,这个人不一定就是个完人,尽管我们的日常教育中,不撒谎是很重要的一项道德品质,我自己也很赞成这种教育,只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注意的是,从来都不撒谎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说白了,文化就是在各种的谎言的衬托之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任何的文化都强调其对社会的一种修饰作用,修饰说白了跟撒谎有结构上的同质性。因此,你可以做一项自我观察,大家应该是每天都在一定程度的撒谎,真真假假才是社会的常态,可以说撒谎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将它叫做文化或文化的一部分。不要扭曲的去理解撒谎,要分辨什么是道德意义上的不诚实与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宽容,这是很重要的“去田野之前”以及“在田野之中”的训练。
二、“扎实描记”
“扎实描记”对于人类学家的基本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心存异趣”是人类学家的基本素质,转化成日常语言就是: 你不要太认真。很多较劲认真的人就没有什么“异趣”。你如果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你看那个女孩儿的屁股长的很好啊”。他就会说: “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流氓。”但是一个人类学家不能像后者这样去思考,因为只有不这样想才能真正考虑到人们对身体的看法,据说乡下的老百姓有一种观察身体的智慧,看女孩子就是看那个部位,然后再决定这个女孩子是否适合做自己的儿媳妇儿。换言之,恪守乡俗的人选择儿媳妇就是看那个地方,别的不看,他看你屁股大不大,背后想的好不好传宗接代,这种看就不是我们今天个体主义的人身伤害意义上的流氓的思考,而是想着那里是管他们家族后代的事儿,也管祖宗的事儿,那就是很重要的社会大事了。在今天越来越把个体价值放在社会之上之后,这种趣味就变成是一种邪恶了,不能为社会接受,当然也就不能公开随便说这样的话了,说了就要负伤害的责任。
可以说有了上述这种专业要求的心存异趣的本领之后,“扎实描记”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用科学的范式来规范你所描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一点正是人类学自身成败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并不是说扎实描记就是人类学的全部,只是八式中的一种而已。你只要经历过这个过程,即写出一部属于自己的民族志作品出来,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写过《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才知道为什么这种方法不是全部,是有它的问题。
描记扎实的程度不仅仅是靠访谈、录音以及录像等记录方式,还可能会有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各类物品、各种空间以及衣食住行诸方面等。有的时候,没有理解上的耐心之人,往往都会直奔主题,不太去关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些可能会更为有助于理解文化存在的真实形态,物比人撒谎的几率终究是小了许多。这种以物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未来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物化的世界,人为物所累,不能不考虑这一层的文化对人的存在而言的意义。而今天的研究也越来越面向现实,而且现在的研究都是靠钱来资助的,没钱似乎就别谈研究。尽管这不是绝对的,但是做田野一定是有一定的金钱做支撑的。当然,完全靠钱支撑起来的研究既有好的,也有一般性的,甚至是很差的,但要做到原创性的不太容易,这往往是从来没有人碰过的主题,有的时候金钱不一定资助到那类题目上去,需要有风险投资的意识才能开展这类的研究。
由扎实描记而写出来的民族志中,《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一部典范。即一个人类学家,不必引用太多任何他人的文章,在一个小地方待上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把自己的扎实描记的观察像写小说一样写下来,并以一个作者的主体存在去做一种对发生的事件的叙事。但它和小说不一样,它是要保证是完全真实的。他的理论最重要的是“田野工作的科学取向”,我称之为“实验室范式”,实际上就是你怎么样去描述像科学实验室里发生的那些反应,只是这里关注的不是物和物之间的接触反应,而是人和人之间往来互动的行为反应及相互的关系结构,这有时甚至要比实验室里描记物理化学的反应更为难于把握,所以在田野里待的时间也比较长,目的就是要去做这种准确地把握。最好的人类学家至少都要待上一年的时间以上,这似乎成为了一个惯例。但应当记住:这种描记并不是最终目的或者不是人类学的全部,人类学更需要思想的发现,这种发现的路径往往都是从边缘的弱者以及微不足道的角度去挑战一些主流的、宏大的看法。马林诺夫斯基所作的一切就是试图去挑战当时的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理性经济,即他的借助扎实描记所指出的“库拉交易”背后的非理性的经济,因此人们之间的交换不单单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表现突出的等价交换、市场逻辑以及理性交换,很多时候人们之间的交换是非等价的,很多是具有象征性的。甚至可以说,库拉告诉我们的乃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中的交换,这种理性的行为背后更多是非理性的做法或观念在做一种支撑,日常生活之中的礼物交换可能就是这种非理性的交换的典型。
人类学要求你一定要住在那里,而不是呆在这里。去那里并住下来,这是保持和当地人有一种融洽关系的前提,这一途径很难把握,需要时间。但今天,很多人试图用钱来完成,用钱雇人做访谈,再分析二手的访谈资料,这种方法在课题满天飞的今天也许是一种做快速研究的通行潜规则,但它在人类学家看来绝对是没有办法的下策。换言之,真正的人类学家不大可能会这么做,不把这当做是标准,而是用一些能使自己融人其中的办法,那才能够有真正的体验和对当地人生活世界的理解,你拿钱去做一种交换,但当地人不是把钱放在第一位的,那你交换回来的就不是他们真实想法。但显然这样的思路自身也在变迁当中。对于在中国从事田野研究的学者中,特别是在乡下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喝酒就是很重要的,甚至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喝了酒,大家就是朋友,不喝酒,对不起,不一定不是朋友,但总是隔着那么一层,进不到当地人的世界里面去,那自然理解也就是差了一层。对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想有扎实描记,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人类学应该是时间的富有者,他可以任情地在田野之中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大概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时间节律中,年度的周期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周期性轮回的基础,即人们的社会生活就是按照这个周期来不断地重复的,因此在人类学中,呆上一年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惯例。在这个一年的周期里,人类学家有可能对当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出一个总体性的描述。
另外,人类学还强调空间,即强调时空坐落下的聚焦观察。在这一点上一个村落可能是容易把握的一个空间范围。它的范围往往大小合适,范围适中。比如做一个诉讼案件的调研,很多人就只是盯着法庭看有没有诉讼,但实际生活中,一个村里女人在街上叫骂,非要找出偷她家鸡的人,因此民间的纠纷解决不是一上来就上诉到法庭上去,由法官来说了算的,那你说这个街头骂人算不算她表达自己的正义理解的一种方式呢?而这是否转而又可以透漏出来当地人解决纠纷的一种风俗呢?至少研究法律的人类学家会认为这算是一种表达正义的途径。还有,很多同学去乡下调查可能是不大会去关心厕所问题的,但人类学家就会关注这个偏僻的地方和人的社会生活的关系。我记得在汶川的羌族村寨里走访时就发现好像自己不会上厕所了,因为,院子角落里就一个厕所,门儿没有插销,你正在上厕所,有人走过来了,那你怎么办?老乡是这样做的,听到来人的声音,里面的人就咳嗽两声,这样事情就解决了。所以,你要学会他们的交往规则,这就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换到城市空间里,这一套就不行了。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实际上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延伸出来的,我们今天专门叫它法律,是因为它本身太复杂了,是在复杂的社会里专门分离出来的一个领域,但在村落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生活里,法律实际是镶嵌在其中的,比如法律就可能是嵌人在当地的宗教之中。
我曾经读过云南大学法学院王启梁教授的一篇文章,文中就提到了“琵琶鬼”,他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去做分析的。[2]而读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实际更为关心的是为什么这个正常的人她会被界定为琵琶鬼。可能她之前曾经是个美女,年纪轻轻地丈夫就死了,当地人在找不出元凶的时候,总会有这样一种归因,把全部的责任都赖在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身上,认为是她的超乎常人的美貌的原因,这背后也可能是社会嫉妒的一种文化的表达。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幸之人,却又被大家所羡慕,羡慕得不到,嫉妒也就会产生出来。这个演绎逻辑社会化之后,那里的人们往往都会把这种逻辑硬塞进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安排中,形成一种整体的社会认知,进而会把这样无端发生的事情,污名化地界定为“琵琶鬼”,或一般意义上的“鬼”。换言之,任何一个社会,无论现在、过去、还是将来,也不论社会规模的大小,都要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制造出一种“鬼”来,以泄元凶找不到以及羡慕得不到的私愤。比如我现在住的小区,过去只要谁家一遭偷窃,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院子里来来往往样貌突出的农民工。实际上这些案件根本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污名化的对象总是那么少数的几类。因此,这个社会里有一套不言自明的逻辑,就是有一些人终究是要变成大家泄愤、宣泄和污名化的对象,社会的一些紧张和危险才能从人的感受上得到一些消解。这种逻辑就是社会与文化的逻辑,而不是法律和宗教的逻辑。
三、“留心古旧”
所谓的“古旧”就是身边留存下来的各种事物。历史就是这样,当你一说话、一写字,它一旦留存了下来了,就会成为一个古旧的东西。但是,我们要从中分辨出来它们的存在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以及在那个这些古旧得以产生的时代人们可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像我在这里所展示的地契、毛泽东的头像等,这些在今天似乎都可以不时在村子里的家户中看到,你看当时这个印有毛主席的头像的照片是可以作为礼物来相互赠送的,现在如果我们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不是那个集体意志高于个体意志的时代是造不出这种交往的方式的。今天时代不一样了,个体觉醒的程度很高,超过了对于集体的认同,这时对于礼物的理解也就不一样了。
还有,对于各种遗存的建筑物也是一样,要把它们都放置在社会建构里面来加以认识。也许大家觉得中国的汉碑或者魏碑,就是汉字,但是你要知道,这可是那个时代人们思考方式的一种反应,我们今天称它们为风格。比如拿汉隶来跟汉代建筑风格做一对比,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就出现了,你看西安的现代仿古建筑也许能看出来一点,建筑像汉隶,汉隶又似那时的建筑,体现了汉代的一种在水平方向上不断去扩张、张扬的气魄。而再看看西方遗存的建筑,因为有长时间的天主教的影响,观念中最高地位的是上帝,那是在往天的高处去追寻,并以之为崇高的居所,也就是跟天进而跟上帝接触。而看看汉代的建筑风格就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平面上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虽然皇帝是天子,但他不是呆在天上的,而是活生生地在人间统治着尽可能广袤的土地和人民,即古语里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四、知微知彰
“知微知彰”出自《易经·系辞下》,所谓“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人类学强调对于微观之处的考察,并强调由这微观而生出来的意义上的差异。借用英国的哲学家赖尔在《心的概念》里提到的“眨眼”的概念,我们应该清楚,眨眼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生理现象,在这个层次上每个人都会表现得一样,具有人和动物的普遍性。但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去考察,你又怎么知道这样一个眨眼动作是一个人因为真的迷了眼睛,还是在含情脉脉地向她的心上人暗送秋波呢?这单单从生理学的层次上去做一种测量是测不出来的。但是,一个男孩儿看一眼一个女孩儿,是轻佻还是喜欢,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大家也都看得出来,这就是文化里才能表达出来的共同意义,是很专门的一种文化的表达。在人类学里,自从格尔茨在1973年出版了《文化的解释》一书,“浓描”的概念就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但是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实际上我们不要简单从“浓描”这两个翻译的字的字面含义上去理解,它还可能有更为丰富的意思,或者说在这浓描之外还有一种中国人擅长的描写方式,就是“轻描淡写”,但轻描淡写并非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浓描。我们的文化里,至少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齐白石那种轻描淡写,那被称之为意境,已经就不一定完全是靠浓描能够反映出来的,反倒是淡抹更能反映出的一种意境。
当然,除了浓描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从蛛丝马迹的线索中引出来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城市中做民族志的话,就不像村落中那么清楚,也就是聚不了焦,现象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所以如何做城市中的民族志,方法就要随着转变,要追溯一种事件发生的线索,慢慢去做一种理解,这是我说的线索的民族志所要求的,对这个问题另有文章叙述,在这里不再细谈。谈个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当下北京的街头人行道上,到处都贴着“包小姐”的小广告,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你对此有好奇之心,那这小广告就是一个线索,依次不断地追溯下去,你就会理解这个广告和整个正式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贴这些广告的人和消费这些广告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一个大的且复杂的社会而言,实际上了解事情发生的线索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个线索你不仅看到了城市的生活,还可能一下子把农村也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你如果顺着这个线索一追溯下去就到了某个村落里面去。这份广告的线索可能是从色情的角度上反映了现在的一些人们在心灵上的一种追求,其中又把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欺骗的因素累加了上来,那样,你对于城市某一部分人生活的理解就会逐渐加深并逐渐扩大你的理解范围。
五、知柔知刚
“知柔知刚”也是典出《易经》,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思维,即不极端也不走极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对于研究者的性格进行过一种分类,他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硬心肠的”,另外一种是“软心肠的”。前者可以归到刚性这一面上来,而后者则是可以算是柔性这一端。就我的观察,凡是那种做社会统计的人,一般都是需要“刚性”的“硬心肠”。而心存异趣的人类学家,往往更多有柔性的“软心肠的”这一面。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是个大概的分类,并且我们要追求的是真正能够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人。
六、神游冥想
这是关于人类学究竟追求什么样的一种境界的问题。开始那几项是要求大家趴下别站起来,做仔细的观察,就像观察两个蛐蛐儿打架,你要趴下去看吧那才清楚,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到了这个神游冥想的阶段,就要求大家去做一种站起来的思考,这实际上是跟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一些对于社会学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批评是有关系的。记得我那时还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8年2月7日上午,在费先生家里,费先生把研究所里的所有人都叫去了,实际是大家都在听他老人家讲话。费先生那时话里话外实际上是在语重心长地启示大家。他说的话原文可以在他的文集里找到,今天回忆起来大概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难道趴下来就不再起来了吗?现在我们要站起来,别趴下,你们的脑筋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不行,不能平面走,一个飞不起来的人他的关系都是平面的,立不起来,现在我们的思想不但要立体化,还要有四五个维度的东西,你们看东西要看到里面去,不能表面上看东西,不要记录下来就算了,背后的那个东西会抓住了就活了。”这并不是原话,是我的记忆的复述。但这记忆对我而言实际上是很深的,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往往都是去到当地,收集数据,然后以为这就是重要的个案资料了,实际上很多人只是把个案罗列在那里,但这很显然没有什么解释的力量。
文化的背后既有近因也有远因,既有宏大的东西,也有细致人微的内容,这些都需要在我们的头脑里做一番仔细琢磨的思考,形成一种让读者感受到有所教益的启示,这也许就是一种费先生所谓的神游冥想吧。比如婚姻的问题,大家可能都觉得,如果相互不喜欢就不会结婚的。但是,我们看一些统计就会发现,比如英国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时候,统计结果就很清楚地表明,只要粮价一上涨,结婚率就上涨,粮价一落下来,结婚率就下降,看起来是个人的行为,实际上背后有一种社会的逻辑,这中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动脑子去想才能想出来。所以,一个小小的村落如何和整个社会以及更大的文化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一种神游冥想的能力。因此,大家不要认为街头广场上的舞蹈就是锻炼身体的,古代人并没有这个概念,舞蹈最初就是沟通人和上天的,这些沟通的动作慢慢地演化成了今天的舞蹈。我们在平面上趴着做田野研究的时候,最终需要有这种超越。文化理解的逻辑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个人就不敢抢银行,但如果有一万个人在一起,有人振臂一呼,可能就会做出来这种社会暴力的行为,只是在于这样一种群体行为是否真的有其发生的条件。比如小的时候一个人不敢走坟地,但是三个人就敢走,这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一种整体观念上的超越。再说一遍,一个村落如何跟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是一个极为需要思考的大问题,这种思考会把人类学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去。
下面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是关于我的庙会研究。你只有在庙里才能真的看到民间社会里人们怎样调解纠纷,这不是在法庭上的纠纷解决,法庭上是另外一种方式。你会看到庙会上有这种现象,华北叫“看香”,点着香之后他会吞到嘴里,出来香还能燃着,这是他最基本的权威表达的方式,如果没这两下子,他根本不可能让人信服。在这里有一种三角形的关系,我叫它做“灵的三角”,即如果香代表神的话,在看香的人和求香者之间就有一个三角的互动关系。你在庙会上会看到来看病的人,她会盯着这个跟她有关的香,香在被看香的人点着之后就是一个燃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所有变化都有着可解释的意义,当地人的这个细节的解释过程,对人类学家就很重要,要做一种扎实的描记。比如,当香燃烧从红突然变黑的时候,这个时候解释就变得很重要,看香的人对这个女士(求香者)说:“你家里有事情”,我想农村妇女除了家里有事,还有什么国家大事吗!这个女士脸色马上就变了,接着看香的师傅说:“你胃不好,”这个时候她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我想胃疼和肝疼,农村人也不一定分得很清楚,但是腹部疼痛是能够感受到的。然后看香的人就说:“这是实病,你也有虚病,家里有老人,你没有照顾好”,这个时候她眼泪就成行成行流下来,为什么?她自己就说了:“我婆婆躺在床上,我看见就烦”,这个时候看香的人会说:“你回去要好好照顾老人,这样虚病就好了。”我想经过看香的人的这番调解之后,她回去不会再对她婆婆不好了,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私心。最后,看香的人还会给她一点儿药,很便宜的,大概是治胃病的药,用来医治她的实病。老百姓在这方面是很实际的,你只要给她一个明确的解释,她觉得灵验了,就会非常相信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宗教在农村会突然有许多信众的原因,背后就是灵验在起作用。当然也有不灵验的,随后这种宗教或者庙宇可能也就逐渐衰落了。
七、克己宽容
我认为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对他者的研究,也就是对你生活之外或者对你而言陌生世界的研究。这里就有一种克己宽容品格的修炼。面对异样的世界,如何去克服自己的不舒服或者不愉快,然后平心静气地观察各种社会反应,这对人类学是很基本的一种学术品质。你去瑶山,当地人给你上山抓一只芒鼠来,那芒鼠看起来比老鼠还恐怖,个很大,说是煮来给你吃,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不吃,你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生活境遇之中去,也无法真正地了解他的世界。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偏见和不宽容,这是心存异趣要加以解决的。还有比如住在北京地道里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流浪汉,很少有人去关怀他们,更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值得追求的。但真正好的学者往往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流浪汉”,我认为如果没有先前的物质的流浪,精神又怎么流浪呢?但研究他们、体会他们以及理解他们,即一种流浪汉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可以给我们生活以启示的一种方式吗!所以,我们没有这份理解,可能都不会成为真正的精神上的流浪者。我们应该从流浪汉的世界里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再想人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这些可能也是我们人类学最应该去思考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你的学科就不仅停留在一种方法的层次上,而是进人到一种真正的哲学层次了。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想这背后的文化意义是未来中国本土人类学可以真正贡献给世界人类学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去排斥所谓的异己,也不应该去排斥与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在那里的文化的存在
。
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在一起》(赵旭东:《在一起: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视野》[3],大家不要看这个词很通俗,似乎是很容易理解,但它却是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其价值的一个概念。可以说,今天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试图让我们彼此分离开来:夫妻本来是在一起的,但是法律的规定是让大家彼此分离开来;因为财产从法理上是属于个人并彼此分离开来的。社会中其他方面的分离就更多了,这方面我讨论的很多,有兴趣可以看看我最近的相关文字。[4]所以,“在一起”这种观念就与社会的分离之道大相径庭,且在今天的社会是值得提倡的。显然,如果医生说你的肺因为有阴影需要切掉,你会说不吗,你不会,你怕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也没有权利选择其他的途径来解决,因为权威和权利都在医生和医院那里。去看牙科最为简单,去的时候可能还是挺好的,患者和医生之间可以寒暄地聊上两句,当医生戴上口罩,然后让你躺到躺椅上去,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人”了,怎么证明你不是人呢?很简单,你躺下以后,医生取出一块用来遮你脸面的蓝布,遮上脸以后,只剩下他要处理的牙齿的圆洞,这样你就是牙齿和身体之间的象征性的分离,这时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就是一个医生要理性去处理的器物而已。西医最近遭到的诟病说到底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能像中医一样有一种对于人的整体性的关怀,并不是说西医本身不好,只是它越来越离人的医学遥远了。其实很多医疗背后都有些巫术的效果存在,病人有时候很相信医生的话,那样身体状况似乎就会慢慢地跟随着改变。说白了,西医对正常的人而言是一种恐怖的存在,很多人应该是被医院的环境吓死的,躺在洁白的床单上,身上到处插着管子,头顶上还挂好几个输液的瓶子,这跟那种望闻问切的传统中医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八、文字天下
我们每个人说白了都是一个写手,只要你想把你看到的、搜集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呈现出来。因此,用怎么的方式来写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文学上叫作叙事研究,在人类学上叫做“写文化”。而中国自己的人类学里有一种说法叫“不浪费的人类学”[5],就是人类学家的笔下没有垃圾,散文、诗歌、摄影等都可以是人类学家的作品,都在反映那个看到的和反思到的文化。显然,不是文字书写都在文学家手里,每个人能用文字来表达的人,都是一个写手,一个作家,他因此怀有的抱负就应当是文字天下,即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形成一种共享的知识,促进文化的融通和发展。我的经验就是,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见闻,每天都要下功夫去写,特别是在田野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写的实践成就了你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理解。因为,很多时候是你的文字决定了你的思考,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文字天下这一点所要真正表达的意义所在。
最近对于田野工作的方法,曾对上面的八式有所拓展,总结出“四统”的工作思路,所谓“四统”就是“点线结合、特征追溯、线面统一、微观聚焦”。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在此过多展开。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人类学为什么会远离江河文明”[6],讨论为什么中国文化里江河文明这样的话语进入不了民族志的描述,我有自己的看法和细致讨论,核心就是基于通过“点线结合”的思路调整而提出来的,供大家阅读批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知识就是从黑暗中透露出来的一丝亮光,只是恰好你把握住了而已。”希望大家都有知识。
( 2014 年8月3日改定于北京四书堂)
参考文献:
[1]赵旭东.“灵”、顿悟与理性: 知识创造的两种途径[J].思想战线,2013,(1):17-21.
[2]王启梁. 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赵旭东. 在一起: 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视野[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24 -35.
[4]赵旭东. 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2):32-48.
[5]稚桐.“不浪费的人类学”思想与实践[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63-69.
[6]赵旭东.中国人类学为什么会远离江河文明[J].思想战线,2014,( 1):68 -76.
【作者简介】 赵旭东(1965-),男,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法律人类学、社会人类学。
via:
-
“田野八式”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网 作者:赵旭东 来 源:《民族学刊》
http://nisd.cssn.cn/ztyj/ztyj_llyff/llyff_ff/201703/t20170302_3438124.shtml
田野调查:经验与误区 ——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2020-11-27 0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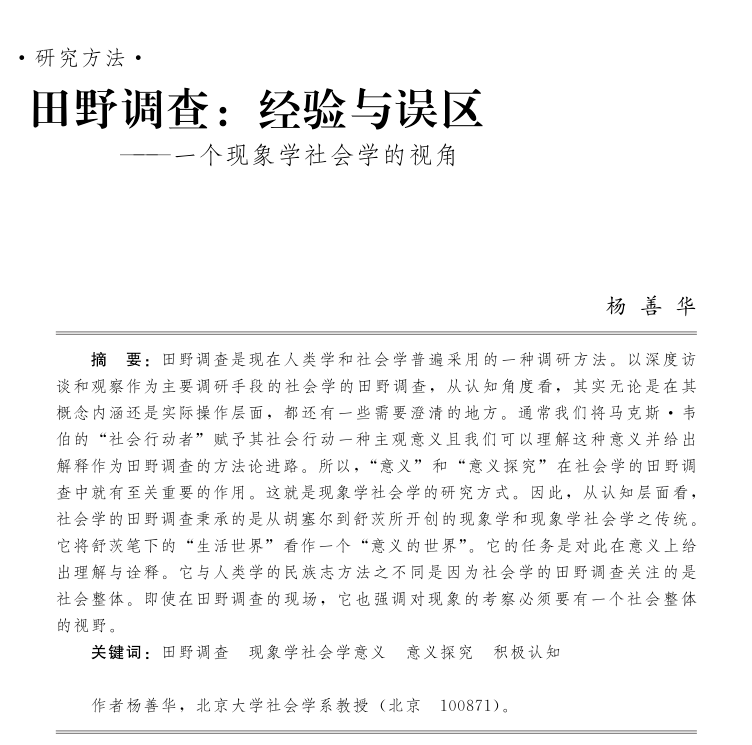
摘要: 田野调查是现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普遍采用的一种调研方法。以深度访谈和观察作为主要调研手段的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从认知角度看,其实无论是在其概念内涵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还有一些需要澄清的地方。通常我们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者”赋予其社会行动一种主观意义且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意义并给出解释作为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进路。所以,“意义”和“意义探究”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因此,从认知层面看,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秉承的是从胡塞尔到舒茨所开创的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之传统。它将舒茨笔下的“生活世界”看作一个“意义的世界”。它的任务是对此在意义上给出理解与诠释。它与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之不同是因为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即使在田野调查的现场,它也强调对现象的考察必须要有一个社会整体的视野。
关键词: 田野调查 现象学社会学意义 意义探究 积极认知
作者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李文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 年第 3 期 P59—P65
一、关于社会学 “田野调查” 的概念
田野调查(fieldwork),是社会学者在做定性研究时普遍采用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但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却跟人类学的民族志有着相当深的渊源。 关于 “民族志” 的概念阐释不一。通常会认为,民族志从文献记录看,会是一个写作文本。但是待马林诺夫斯基在 1914 年从澳大利亚出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新几内亚去调查,出版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系列著作,并为 “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 确立了 “必须做到搜集材料的主体和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 这样的准则之后,民族志也意味着是一种田野调查方法。
由此,大卫・费特曼(David M. Fetterman)在《民族志:步步深入》一书中认为,“民族志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民族志学者 “带着开放思维而非脑袋空空进入田野”。费特曼还指出,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一样,民族志学者 “一开始也会对人们如何行为和思考存在倾向或先入为主的观念”。为了减轻倾向的负面影响,民族志学者 “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倾向”,而 “一系列额外的品性控制,如多方检验(triangulation)、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以及价值无涉的取向,给倾向的负面影响加了一道控制阀”。马里兰大学教授厄弗・钱姆伯斯(Erve Chambers)进一步指出,民族志的目标是 “描述与解释人类事务中的文化地位”,因此,“民族志主要应以其研究对象来界定,即民族与文化,而非以其方法论来界定。”
故由以上对民族志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志的聚焦点或者说研究对象是文化。
之所以要将人类学的民族志做一个如此详细的介绍,是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将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也称之为田野调查,但是实际上这个 “田野调查” 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然而我们通常又将田野调查看作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只要提了它别人就都能理解。 按陈向明教授在《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中的说法,“中国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常用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与她在书中所探讨的 “质的研究方法”“十分类似”,或者说 “质的研究方法就是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在该书第 2 章 “质的研究的历史发展” 中讨论了质的研究的分期,她借用别人的评价,认为现代主义期(1950—1970)是质的研究的 “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质的研究受到现象学和诠释学的影响。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陈向明对 “质的研究方法” 给予的定义强调了质的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情境性和关联性。
从田野调查实践这个维度看,笔者基本同意陈向明对质的研究方法所下的定义。但是,笔者认为,陈向明没有突出田野调查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就是 “意义”。 诺曼・K. 邓津与伊冯娜・S. 林肯(Norman K.Denzin, Yvonna S.Lincoln)在《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的《导论》部分对定性研究的定义中指出:“定性研究…… 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现象。”
由上文邓津等人对定性研究的定义可见,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的核心。这就使我们很自然地将这样的定性研究置于马克斯・韦伯的 “理解社会学” 的范围之内,因为正是他认为,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主观意义。因此,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对 “社会学” 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学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和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从而将对社会行动给出 “解释性理解”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和重要方法,这就为定性研究所说到的对现象的意义之理解和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阿尔弗雷德・舒茨则在对韦伯提出的理解 “社会行动” 的意义这一见解的批判中进一步发展了如何理解和解释人们赋予现象的 “意义” 这一问题,他将 “理解” 界定为 “意义的关联”(correlative to meaning),这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是对意义的理解,同时所有的理解都是意义。因此,如果田野调查是探寻人的社会行动的意义,那么对这种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将贯穿整个田野调查的始终。
那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民族志的社会实践部分)有无区别?笔者认为,至少可以说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区别:(1)从关注点来说,民族志关注的是文化,即使是对社会的关注或者说欲对社会现象给出解释,也是经由文化这一进路。 而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它考察社会现象时有一个整体性的视野),在社会整体之下它也有一些现在已经变成传统的研究领域,比如社会结构(阶级和分层、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社会冲突、社会问题乃至像经济与政治等分支社会学,社会文化当然也是它的一个关注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关注点),但也仅此而已。因此,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在农村的调查)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当年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农村所做的社区研究。(2)社会学虽然也强调将观察作为收集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料的方法,但是它很少会采用民族志的参与性观察。 因为参与性观察的成本相对要高很多。所以笔者在与孙飞宇合作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中强调的是在访谈现场(或者说田野调查现场)的全方位的观察,至于参与性观察的作用 —— 通过建立 “我群关系” 和信任关系来获取真实信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则可以通过对某地的追踪调查来实现。
由以上分析笔者可以对社会学田野调查给出一个初步和简略的定义: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是以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在田野现场自始至终的意义探究为特征的情景性活动,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并因此而包含着一种对社会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研究者是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获得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的解释性理解,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社会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
二、经验
这里所说的经验,主要是笔者和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从事社会学田野调查实践二十余年所感悟到的若干体会。
**首先,这样的田野调查必须具备一种 “积极认知” 的态度。**从前面的分析可知,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基础是包容了现象学、诠释学立场的现象学社会学。而现象学要重点讨论的就是认知问题。因为认知在哲学中就属于认识论讨论的范围。在哲学的发展中,其实一直没有解决的是如何从 “个别过渡到普遍,从现象过渡到本质” 的问题。胡塞尔在阐释现象学的时候讲到 “本质直观”,按张祥龙教授的说法,这种本质直观的本义就是 “在个别中直接看到普遍,在现象中直接把捉到本质”,以此来 “解决自古以来困扰和激动着西方哲学主流的核心问题”。而他讲的本质与 “柏拉图主义的抽象的、概念化的本质” 是 “不一样的”。这个 “本质” 已经与 “现象” 从实质上沟通起来了。陈向明教授在前边谈现代主义期现象学的影响时也提到 “现象学认为本质就是现象”,但是她没有指出何为本质。笔者认为,要讨论现象中的本质,“意义” 问题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张祥龙指出,“意义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盲点”。“这就是胡塞尔在《小观念》一开始讲到的为什么传统西方哲学包括科学都解决不了认识论问题的原因”。所谓认识论的问题,最终也应该是 “意义如何可能” 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本质,最核心的应该就是与 “纯粹现象” 在一起的、决定了现象性质的现象之意义。
由此出发,所谓的 “积极认知” 态度就是,当你来到田野现场之后,你感受到现场的种种现象(包括你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环境)之后,你不能说我只观察到了现象,而没有感知(或者借用胡塞尔的概念 “直观”)或直观到与现象在一起的 “现象的意义”。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的某个学生去做访谈,他回来跟我说,“杨老师,这个被访人没有讲出什么”。要是在没有知晓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并将其作为我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思想之前,我会接受学生的说法,但是在接受了之后,我就一定会跟学生说,被访人按韦伯的说法,是不是社会行动者?如果是,那么被访人与你的谈话以及你看到的访谈环境是不是被我们的被访人赋予了意义?如果这些都存在,那么你说没有讲出什么是不是就是你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有问题?所以,“积极认知” 的态度在田野调查中有时候可以起到追逼研究者刨根问底,不把事情弄清楚(找到现象背后的意义)不罢休的作用。
其次,把田野调查看作意义探究的过程,就意味着田野调查不再只是一个收集资料的过程,同时还是从进入田野现场就开始感知和分析自己所感受到种种社会现象的过程。 如果把狭义的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视为深度访谈加上全方位的观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进入田野现场就意味着研究的开始。笔者认为,这样一种见解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将调查和研究真正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了一个研究者在从田野现场回来后面对卷帙浩繁的访谈资料产生一种无从着手的感觉。因此,从田野调查的执行层面而言,贯彻上述将进入田野现场就看成研究开始的见解无疑是一场革命。
再次,是意义的辨析和区分。上文提到的感知,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即获得 “相关材料” 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然而从我们研究的学科特征来说,我们应该获得的是材料的社会学的意义。所以,意义的辨析与区分就是在感知的同时将有社会学意义的材料从所有的材料中分离出来,并争取完成研究层面的提升 —— 争取由经验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做出一个带有经验层面的鲜活的理论概括。
而这样的感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 “本质直观” 的一部分,是本质直观的内在基础;所以说到底,本质直观并不外在于原初感知(不是对于感知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而只是通过观察目光的调整而改变统握感知材料的方式罢了,也就是从感觉直观的方式转变为概念直观或范畴直观,发现更高层的关系结构。我们要选择的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普遍性的材料,而这样的普遍性显然是具有 “类本质” 的属性的,但又是浸泡在原初的感知场之中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田野现场的深度访谈,通常我们要问被访人的生活史,但事实上每个被访人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是会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的。这个自我定位就是他 / 她认定的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这就关涉到社会分层,社会学的意义也就由此凸显。2002 年笔者在北京后海做田野调查,访问过一个姓姜的老太太。她坐姿自然挺拔,显出训练有素,形象干练,令知道一点老北京故事的笔者马上浮现出一个想法,这个老太太 “在旗”(满族对自己身份的说法)。在笔者把问题往这上面引的时候,老太太就非常自豪地说了,自己是 “镶黄旗” 的。“镶黄旗” 在 “满八旗” 当中属于 “上三旗”,相对 “下五旗” 要尊贵。这个时候老太太自豪的神情就充分表明了她知道镶黄旗在满八旗中所处的地位,由此自然也让我们看到了老太太的自我定位。因此,其时她的陈述也就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最后,是关注对现实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中 “盲点” 与悖论的洞察。 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点就是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其原因则是因为生活世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这样的想当然地接受这种现实,既是社会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比如社会风俗),又是一些误解得以长期存在从而变成盲点的缘由。比如 “留守家庭” 和 “空心村” 的问题,这本是大批农民工外出打工后人们的观察,但是因为观察的时点性,观察者没有看到这些外出打工者依然保持着和流出地自己生活的村庄的密切联系。这些联系不仅是往家里寄钱的问题,还有年终返乡时参与村庄的种种活动以及他们将村庄作为自己社会竞争的主体舞台的意识及由此而来的行动。我们 2017 年和 2019 年春节后在四川宜宾农村的调查发现了这一点,看到打工仅是家庭谋生的一种策略,归根到底,这些村民还是要回到流出地自己的家中。这尤以 40 岁左右的中年人为最。因此,在这些地方,所谓的 “空心村” 就是一个属于盲点的概念。
三、误区
在田野调查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听到一些案例,让我们觉得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层面,还存在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就是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现场的视角与立场的问题 —— 不能站在被调查者立场上来做出 “投入的理解” 和 “同感的解释”。 就如农村问题而言,就存在对 “农村实际” 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即学者或官员眼中的 “农村实际” 与实际生活于其中并对此有切身感受的农民眼中的 “农村实际”。这两种实际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过,要真正了解农村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就 “必须知道农民眼中的‘农村实际’,而不是用学者或官员眼中的‘农村实际’来代替农民眼中的‘农村实际’。”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作为政策受众的农民的实际感受,从而对政策实施的效果给予评估,也才能对农民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的解决给予真切有效的帮助。
因此,在进入农村做田野调查时,事实上可以有三种视角和立场:学者的、政府官员的和农民的。而要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必须采取农民的视角和立场。
**误区之二,是价值先行或概念先行。**这是笔者的说法,意指研究者在进入田野现场之前,已经预设了自己的判断和想要证明的东西,进入现场之后,只是寻找符合自己价值和想法的材料,而将所有不利于证实自己判断和概念的材料一概进行 “选择性过滤” 然后加以抛弃。这就像前边费特曼说民族志学者及别的学者那样,他们 “一开始也会对人们如何行为和思考存在倾向或先入为主的观念”。刘成斌将这种现象称为 “盆景主义”,即 “拿着自己读书时获得的理论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样去裁剪经验材料”。这就在调查方法论上违背了胡塞尔提出的 “悬置” 原则。
所谓 “悬置”,在胡塞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中止自然态度下的判断,“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并由此,“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学”,尽管它们依然有效,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包括真理(即暂时中止研究者原有的自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按胡塞尔的看法,只有在经过这样的悬置之后,我们才能直观到经过悬置实现现象学的还原之后的 “纯粹现象”,才能获得对这样的纯粹现象意义的认知和洞察,才能避免价值先行和概念先行带来的理论概括的偏颇。因此,“悬置” 是获得对 “真实” 的认识的前提。而违背 “悬置” 原则的后果是,由于进入田野调查现场后考察视角存在某种片面性,由此产生的判断与得到的结论都可能因为这种片面而被别的研究者以他们实地调查获得的与此相悖的个案而被驳倒,这也是我们为何在进入田野现场时必须抛掉我们的成见和理论假设,只是全身心地感受被调查者的原因。
误区之三,是在遭遇 “罗生门”,即主体经历阐释的异质性(即俗语所说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因缺乏对事件的真实性的全面把握而陷入相对主义(若都是真的,那到底何为真),从而对访谈材料的真实性产生根本性的怀疑。 在访谈中确实我们会遇到 “对同一事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阐释”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河北省农村调查时,曾经在访谈中听与一起青年妇女自杀事件有关联的人员谈及这件事,结果每个人说话时的立场及谈话口吻、对事件情节的描述和原因分析都有所不同。凡是女方娘家的亲戚,都认为该女子自杀是其婆家的责任,过错在婆家,凡是其婆家这边的人,虽然也对该女子自杀表示惋惜,但认为其轻生亦有自己的过错,婆家虽有责任,但不能说是婆家害死了这个女子。而既不属于娘家也不属于婆家的,口气则相对超脱,立场恰似在中间,但其对事实的陈述则因其隔得太远而不甚清楚。
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发之一是,对于这样的社区中发生的公共事件,被访人的立场一定会因其与此事件的利害关系而产生倾向性。 他们会本能地宣讲事件中对自己有利的这部分事实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导致事实真相被歪曲。
启发之二是,由此可以设想,凡访谈得到的资料,因其是经由被访人陈述得以呈现,故一定经过被访人主观的加工,因而是意义建构的产物。 即使我们从里边获得的真实,那也只是一种 “意义的真实”(当然,这种 “意义的真实” 也是真实)。这就跟以前我们的理解 ——“真” 就是 “事实”—— 有着重大的不同。
总结
最后,笔者想用自己在《感知与洞察: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一文中的一段话来为本文做一小结:
归根结底,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对世界或者对社会的终极认识或者终极理论。按其本意,它提供的只是我们认识胡塞尔与舒茨都将其看作研究的重心的生活世界的原则与通路(当然也可以包括我们研究与分析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某些方法论与方法方面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社会学是开放的,就像现象学是开放的一样。我们要完成的只是按照多姿多态的生活本身来认识生活这样一项任务,而这可以借用现象学的一句话来概括 —— 朝向事情本身。
via:
-
田野调查:经验与误区 —— 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_研究 中国学派 2020-11-27 09:18
https://www.sohu.com/a/434644177_488440



















